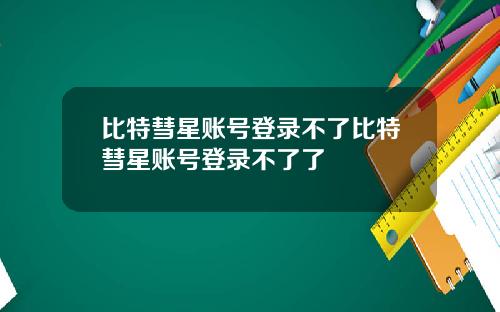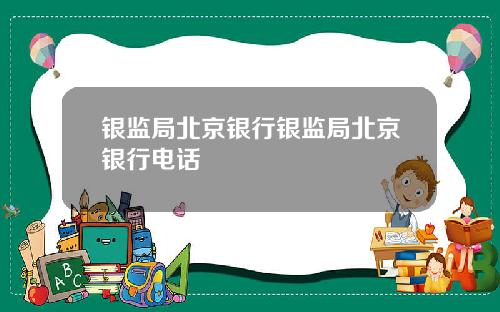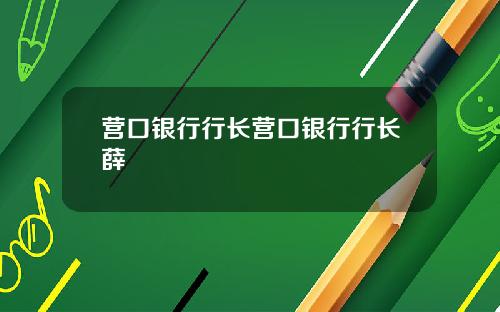在当今社会,由于证券市场交易的快捷性、自动化,使得一些 针对公民证券利益的犯罪行为显得更加隐蔽性和便捷化,
侵入他人股票账户买卖他人股票成为此类犯罪行为中最常见的一种犯罪行为。
一、案例摘要
被告人钱某在某证券营业部交易大厅,通过偷看、猜测的方式前后获取了张某、李某等十余人的股票账户及交易密码后,
通过电话或者证券交易大厅的电脑操作的委托方式。
在张某、李某等十余人的股票账户上高买低卖某一股票,同时通过自己开设的股票账户低买高卖同一股票,从中谋取股票差价,
前后共给张某、李某等十余名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三十余万元,钱某前后共获得非法利益十余万元。
二、法院审理
本案件由某省中级人民法院以钱某构成盗窃罪作出一审判决,后钱某上诉于某省高级人民法院,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钱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三、案件分析
钱某的整个犯罪过程主要包括为转移被害人股票的准备行为和转移被害人股票的实际行为两部分。为转移被害人股票的准备行为包括:
行为人非法获取被害人股票账户及交易密码的行为、擅自委托证券经纪商对被害人账户内的股票进行竞价交易的行为。
实行行为是主要表现为行为人通过自己的原有账户与盗取的被害人的股票账户达成交易的行为。钱某非法获取张某、李某等十余人的股票账户及交易密码后,
客观上便拥有对十余名被害人股票账户内的股票的控制权,可以随意委托证券经纪商进行买卖。
在法律意义上钱某已经排除了股票原权利人的占有并可以以自己的意愿处分这些股票,这是行为人控制被害人的股票为随后的转移被害人股票做准备的行为
。表面上看起来行为人的行为似乎符合盗窃股票的行为特征,其实不然。
股票作为股份有限公司颁发给出资人的一种出资证明,股票本身并没有价值,其记载的出资人的相关财产权利才是股票价值的真实体现,
所以钱某的行为实质并非是盗窃股票而是窃取被害人的相关财产权利,但股票价格的涨跌也正是这些财产权利价值大小变化的直接反映。
而本案中钱某实施的一系列违法行为都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根据股票本身及其交易流程的特征,
钱某在控制他人股票后直接进行正常的股票交易并不一定会给他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甚至可能会导致其财产的减损。
所以,本案中钱某在控制了张某、李某等十余人股票账户及交易密码后并没有采取冒险的正常股票交易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
钱某为获取非法利益采取的是另一种更为稳妥的牟利方式。
即通过与自己控制的另一个股票账户进行交易,在股票交易过程中将自己持有的冷僻股高价卖给被害人、
低价买入被害人持有的优势股,最终达到侵财目的。
在实施整个自我交易过程中,买卖过程完全是按照证券交易流程的规定进行操作,都是通过在证券交易所竞价成交的方式达成交易。因此,
钱某的行为符合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特征,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实施行为时钱某虽然对盗窃数额不会有确切的认识,但是钱某自身作为股票投资者之一,
在盗买盗卖被害人股票时应该对其行为所能造成的损失具有清醒的认识,即意识到自己在盗窃较大数额的财物。
客观上钱某通过一系列的准备行为和实行行为最终窃取了被害人的股票,给被害人造成三十余万元的损失
。在钱某非法侵入被害人的股票账户内时钱某已经排除被害人对股票的占有。
钱某将被害人的股票擅自委托证券经纪商进行集中竞价交易的行为属于钱某在排除被害人对股票控制之后的利用被害人股票的行为,
最后无论是在钱某通过自己的账户与自己达成交易时还是与第三人达成交易时其盗窃行为均已完毕。
而最终钱某获利与否均是其排除、利用被害人财物的结果,对盗窃行为的完成形态及盗窃数额不具有影响,
所以综上所述,钱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既遂的本质特征,应当以三十余万元认定盗窃数额。
本案中涉及的行为人的犯罪方式充分说明当代资本证券化、证券电子化的特点,在对此社会特点下的犯罪行为的认定过程中,司法机关要善于剖解复杂的证券运作流程,
要在传统的犯罪行为基础上正确定位新生事物的‘角色’,如此方能正确判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